关于隐痛
版主: huangchong
#1 关于隐痛
宰相裴居道沉湎于女色。
他才四十七岁,与其它几位宰相比起来,他最年轻。
他虽然是以将军入仕,但他对打仗没什么兴趣,对权谋也没有兴趣,没什么雄心壮志。他家世不错,出自河东裴氏,是名门望族,祖父、父亲都是高官。
他起初也清简自持,善教子女。女儿因为美丽又有家教,被高宗皇帝聘为李弘的太子妃。
李弘暴病过世,女儿从此守了活寡。这让人怎么说!
裴妃自此无声无息。她敛眉含笑的模样儿只能长存梦里了。她的寝殿供着李弘的牌位,裴卢氏每年进宫探望,回府唯流泪而已。
裴居道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五个兄弟眼看着娴静的姊妹活生生地憔悴下去,不会不形于颜色。
他们的父亲能怎么样?
裴居道的儿子们也不让人省心,二儿子裴溓、三儿子裴润白衣无职。
初唐举荐成风,裴居道身居高位,河东裴氏入仕的人很多。同族裴炎更是先于裴居道任宰相,权重一时。裴居道这两个儿子,他居然推举不出去!
养儿女有什么用呢?孩子长到什么年纪,就有什么年纪的愁烦。好不容易到子女成年可以放手了,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把人打懵了!而且就此绝望,再无翻身可能!
他还算好的。裴溓和裴润还年轻,也许还有机会。韦待价的弟弟韦履冰,也是白衣,胡子已经花白了。韦履冰歪嘴。一辈子也做不了官。朝廷不要形貌不够端正的人当官,有伤大国体面。
想到裴府这两个不成器的东西也许会象韦履冰一样白衣到老,也一样绝望!
他自己也让人伤心。上朝一看其他几个宰相就知道了。裴居道要资历没资历,要才学没才学,天后提拔他,因为他是国丈。
前两年与岑长倩、韦方质一起筹备发布《垂拱格》,常与两位交谈。有时岑长倩与韦方质辩论起来,他竟然插不下话去!他觉得两个人讲的都有道理!有时两人引经据典,说的也是唐音,是什么意思,他竟然听不懂!
他不能算胸无点墨,但毕竟是在笔上心怯。前些年改职的时候,连谢表也是请才子写的。
朝野不是没有声音说他无能。最刺痛人的说法,他的宰相之位是女儿一辈子的青春换来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忧心女儿,妻子裴卢氏日夜拜佛,家事渐渐撒手,也不爱修饰自己。日常见面,只有几句寒暄。
丈夫都做不好!
想起来心里会抽痛。
裴居道心悸晕厥过一次。医生说不宜思虑过度。心悸这种病,随时会死。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不如享受当下!
窦姜姬敞开着裙子,挑逗道:“再来?”
裴居道暧昧地看着窦姜姬的长辫子,抚摸着窦姜姬光裸的背脊说:“喂不饱你?”
窦姜姬道:“相爷还行吗?”
年近半百的裴相爷翻身又压了上去。
窦姜姬=豆浆机
标签/Tags:
#5 Re: 关于隐痛
宰相裴居道沉湎于女色。
他才四十七岁,与其它几位宰相比起来,他最年轻。
他虽然是以将军入仕,但他对打仗没什么兴趣,对权谋也没有兴趣,没什么雄心壮志。他家世不错,出自河东裴氏,是名门望族,祖父、父亲都是高官。
他起初也清简自持,善教子女。女儿因为美丽又有家教,被高宗皇帝聘为李弘的太子妃。
李弘暴病过世,女儿从此守了活寡。这让人怎么说!
裴妃自此无声无息。她敛眉含笑的模样儿只能长存梦里了。她的寝殿供着李弘的牌位,裴卢氏每年进宫探望,回府只是流泪。宫宴时裴居道把自己修饰整齐,随班赴宴。高台上灯影辉煌,丽人穿梭,可是,压根见不到女儿的身影。他回府说:“皇家医药,非同小可。看起来陛下健康无恙,圣人英姿焕发,令人欣喜。”
裴卢氏呆望着他,“啊”地应了一声。他非常心虚,试探着问:“女儿怎么样?”
裴卢氏又哭了。她这几年老得也特别快,皮肤松弛,没有光彩。
裴居道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五个兄弟眼看着母亲,不难想象娴静的姊妹在活生生地憔悴下去。
他们的父亲能怎么样?
裴居道的儿子们也不让人省心,二儿子裴溓、三儿子裴润白衣无职。
初唐举荐成风,裴居道身居高位,河东裴氏入仕的人很多。同族裴炎更是先于裴居道任宰相,权重一时。裴居道这两个儿子,他居然推举不出去!
养儿女有什么用呢?孩子长到什么年纪,就有什么年纪的愁烦。好不容易到子女成年可以放手了,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把人打懵了!而且就此绝望,再无翻身可能!
裴溓和裴润还年轻,也许还有机会。与他同为宰相的韦待价,弟弟韦履冰一辈子也做不了官!韦履冰也是白衣,胡子已经花白了,他歪嘴。朝廷不要形貌不够端正的人当官,有伤大国体面。韦待价根本就没费事跟任何人举荐他!
裴溓和裴润很愿意父亲带他们会客。因为可以趁机购置衣物,挑拣吃用,让日子过得更舒服一点。裴居道让他们多读书,裴溓答道:“父亲,难道官职是读书读出来的吗?”
裴居道说:“你们给妹妹写封家书也好,一点一滴,也是你们的历练。”
裴润道:“妹妹的事家书可安慰不了!”
裴居道说:“手足相连,你们写信给她,她也许想想其他的事。”
裴润道:“能想什么其他的?想出宫来玩儿?想回家?”他笑起来:“父亲猜她回信说什么?请兄长勿以本宫为念?”
裴居道喝一声道:“住口!”
裴溓道:“父亲,三弟是有道理的。与宫中书信往来,倘若惹出嫌疑来,那是覆巢之祸!”
不是危言耸听,裴炎不是覆巢了吗?
可是裴炎必将名留青史,这两个衣着光鲜的孽子,跟他怎么能比?他们丝毫感觉不到父亲的轻蔑,还在大言炎炎地指点他!
想到裴府这两个不成器的东西也许会象韦履冰一样白衣到老,也一样绝望!
他自己也让人伤心。上朝一看其他几个宰相就知道了。裴居道要资历没资历,要才学没才学,天后提拔他,因为他是国丈。
前两年与岑长倩、韦方质一起筹备发布《垂拱格》,常与两位交谈。有时岑长倩与韦方质辩论起来,他竟然插不下话去!他觉得两个人讲的都有道理!有时两人引经据典,说的也是唐音,是什么意思,他竟然听不懂!
朝野不是没有声音说他无能。最刺痛人的说法,他的宰相之位是女儿一辈子的青春换来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忧心女儿,妻子裴卢氏日夜拜佛,家事渐渐撒手,也不爱修饰自己。日常见面,只有几句寒暄。有时裴居道问她祈祷了什么,裴卢氏说:“祈祷佛祖保佑。”
裴居道说:“不须祈祷,说出来裴某就办得到。”
裴卢氏怜悯地看他一眼,安慰地说:“那当然!佛祖保佑,郎君不是有意亵渎。”
裴居道说:“我不是虚言,天灾人祸,人力不可挽回,不须求神拜佛。可以找得到的欢乐,那就努力去找。”
裴卢氏道:“郎君厚意,妾身心领了。的确有一件事,要与郎君说一下。”
裴居道略觉欢喜,说道:“请讲!为夫尽我所能!”
裴卢氏迟疑片刻,开口说:“郎君啊!丑事的话,别要闹得众人皆知比较好!”
裴居道道:“你什么意思?”
裴卢氏低声道:“妾身不是怪你。每次宫宴,那些武将,个个都忽然会写诗了?不都是找人代写的嘛!偏偏天下人单知道裴相爷胸无点墨,写谢表不会写,满城去找人写。不是有点让人难堪吗?”
前些年裴居道改职,谢表是请苏味道写的。
裴居道脸红到脖子根儿上,爱怜之意消得干干净净。他说:“我不是不会写,是怕露怯。再说,从左金吾将军再任左金吾将军,连官名都没变,为什么要多写一篇谢表呢!案牍之间,使人疲累。”
裴卢氏点头说:“那是自然。其实妾身,妾身也可以代笔。免得传出去被人批评。”
丈夫都做不好!
想起来心里会抽痛。
裴居道心悸晕厥过一次。医生说不宜思虑过度。心悸这种病,随时会死。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不如享受当下!
窦姜姬拉着衣襟挑逗道:“相爷还有意吗?”
裴居道暧昧地看着窦姜姬的长辫子,抚摸着窦姜姬蜜糖般的肌肤说:“既得陇,复望蜀。”
窦姜姬道:“不是妾身诱敌,是相爷空城吧?!”她身上有丝丝寒意,话声也不无讥诮。
年近半百的裴相爷又扑向了花间的无形之境。
捕食也是一种优雅
看穿混沌的能力
柔软中藏着坚硬的智慧
能在极限中扎根的生命
都为造物所欢喜
不捕食就滑翔
象孤独在海面上写字
把风暴远远抛在脑后
速度紧紧跟随着意志
有时候冲锋就是投降
逃避还是逃避
命运要捕食
理由没人知
——《塘鹅》
#6 Re: 关于隐痛
怎么 一边润色一边发表吗?pmsy 写了: 2025年 7月 8日 11:28 关于隐痛
宰相裴居道沉湎于女色。
他才四十七岁,与其它几位宰相比起来,他最年轻。
他虽然是以将军入仕,但他对打仗没什么兴趣,对权谋也没有兴趣,没什么雄心壮志。他家世不错,出自河东裴氏,是名门望族,祖父、父亲都是高官。
他起初也清简自持,善教子女。女儿因为美丽又有家教,被高宗皇帝聘为李弘的太子妃。
李弘暴病过世,女儿从此守了活寡。这让人怎么说!
裴妃自此无声无息。她敛眉含笑的模样儿只能长存梦里了。她的寝殿供着李弘的牌位,裴卢氏每年进宫探望,回府只是流泪。宫宴时裴居道把自己修饰整齐,随班赴宴。高台上灯影辉煌,丽人穿梭,可是,压根见不到女儿的身影。他回府说:“皇家医药,非同小可。看起来陛下健康无恙,圣人英姿焕发,令人欣喜。”
裴卢氏呆望着他,“啊”地应了一声。他非常心虚,试探着问:“女儿怎么样?”
裴卢氏又哭了。她这几年老得也特别快,皮肤松弛,没有光彩。
裴居道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五个兄弟眼看着母亲,不难想象娴静的姊妹在活生生地憔悴下去。
他们的父亲能怎么样?
裴居道的儿子们也不让人省心,二儿子裴溓、三儿子裴润白衣无职。
初唐举荐成风,裴居道身居高位,河东裴氏入仕的人很多。同族裴炎更是先于裴居道任宰相,权重一时。裴居道这两个儿子,他居然推举不出去!
养儿女有什么用呢?孩子长到什么年纪,就有什么年纪的愁烦。好不容易到子女成年可以放手了,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把人打懵了!而且就此绝望,再无翻身可能!
裴溓和裴润还年轻,也许还有机会。与他同为宰相的韦待价,弟弟韦履冰一辈子也做不了官!韦履冰也是白衣,胡子已经花白了,他歪嘴。朝廷不要形貌不够端正的人当官,有伤大国体面。韦待价根本就没费事跟任何人举荐他!
裴溓和裴润很愿意父亲带他们会客。因为可以趁机购置衣物,挑拣吃用,让日子过得更舒服一点。裴居道让他们多读书,裴溓答道:“父亲,难道官职是读书读出来的吗?”
裴居道说:“你们给妹妹写封家书也好,一点一滴,也是你们的历练。”
裴润道:“妹妹的事家书可安慰不了!”
裴居道说:“手足相连,你们写信给她,她也许想想其他的事。”
裴润道:“能想什么其他的?想出宫来玩儿?想回家?”他笑起来:“父亲猜她回信说什么?请兄长勿以本宫为念?”
裴居道喝一声道:“住口!”
裴溓道:“父亲,三弟是有道理的。与宫中书信往来,倘若惹出嫌疑来,那是覆巢之祸!”
不是危言耸听,裴炎不是覆巢了吗?
可是裴炎必将名留青史,这两个衣着光鲜的孽子,跟他怎么能比?他们丝毫感觉不到父亲的轻蔑,还在大言炎炎地指点他!
想到裴府这两个不成器的东西也许会象韦履冰一样白衣到老,也一样绝望!
他自己也让人伤心。上朝一看其他几个宰相就知道了。裴居道要资历没资历,要才学没才学,天后提拔他,因为他是国丈。
前两年与岑长倩、韦方质一起筹备发布《垂拱格》,常与两位交谈。有时岑长倩与韦方质辩论起来,他竟然插不下话去!他觉得两个人讲的都有道理!有时两人引经据典,说的也是唐音,是什么意思,他竟然听不懂!
朝野不是没有声音说他无能。最刺痛人的说法,他的宰相之位是女儿一辈子的青春换来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忧心女儿,妻子裴卢氏日夜拜佛,家事渐渐撒手,也不爱修饰自己。日常见面,只有几句寒暄。有时裴居道问她祈祷了什么,裴卢氏说:“祈祷佛祖保佑。”
裴居道说:“不须祈祷,说出来裴某就办得到。”
裴卢氏怜悯地看他一眼,安慰地说:“那当然!佛祖保佑,郎君不是有意亵渎。”
裴居道说:“我不是虚言,天灾人祸,人力不可挽回,不须求神拜佛。可以找得到的欢乐,那就努力去找。”
裴卢氏道:“郎君厚意,妾身心领了。的确有一件事,要与郎君说一下。”
裴居道略觉欢喜,说道:“请讲!为夫尽我所能!”
裴卢氏迟疑片刻,开口说:“郎君啊!丑事的话,别要闹得众人皆知比较好!”
裴居道道:“你什么意思?”
裴卢氏低声道:“妾身不是怪你。每次宫宴,那些武将,个个都忽然会写诗了?不都是找人代写的嘛!偏偏天下人单知道裴相爷胸无点墨,写谢表不会写,满城去找人写。不是有点让人难堪吗?”
前些年裴居道改职,谢表是请苏味道写的。
裴居道脸红到脖子根儿上,爱怜之意消得干干净净。他说:“我不是不会写,是怕露怯。再说,从左金吾将军再任左金吾将军,连官名都没变,为什么要多写一篇谢表呢!案牍之间,使人疲累。”
裴卢氏点头说:“那是自然。其实妾身,妾身也可以代笔。免得传出去被人批评。”
丈夫都做不好!
想起来心里会抽痛。
裴居道心悸晕厥过一次。医生说不宜思虑过度。心悸这种病,随时会死。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不如享受当下!
窦姜姬拉着衣襟挑逗道:“相爷还有意吗?”
裴居道暧昧地看着窦姜姬的长辫子,抚摸着窦姜姬蜜糖般的肌肤说:“既得陇,复望蜀。”
窦姜姬道:“不是妾身诱敌,是相爷空城吧?!”她身上有丝丝寒意,话声也不无讥诮。
年近半百的裴相爷又扑向了花间的无形之境。
捕食也是一种优雅
看穿混沌的能力
柔软中藏着坚硬的智慧
能在极限中扎根的生命
都为造物所欢喜
不捕食就滑翔
象孤独在海面上写字
把风暴远远抛在脑后
速度紧紧跟随着意志
有时候冲锋就是投降
逃避还是逃避
命运要捕食
理由没人知
——《塘鹅》
#7 Re: 关于隐痛
裴居道用过晚餐,去书房盘桓了一会儿,回了卧房。
他的妻子裴卢氏居然也在!还有他的小孙子。
裴居道惊奇地说:“你们又来了!”
昨天裴立心随奶奶来玩,裴居道陪孙子玩了一会儿,尤烟姬进来陪侍。裴卢氏与小立心逗留到很晚,尤烟姬要告退。裴居道欲火中烧,不得不赶妻子回房。
今天又来了!
立心是裴居道长子裴汪的儿子,跟刘祎之的孙子刘思翔差不多大。他坐在床上,在玩裴居道的玉如意。
裴卢氏道:“姊妹来了,我把卧房让给了她。”
裴居道说:“谁?”
裴卢氏道:“厍狄族嫂。”
裴厍狄氏是裴行俭的继室。裴行俭虽然已经亡故,他生时战绩卓著,惠及后人,厍狄氏也很得族人尊敬。
裴居道的侍妾洪甘姬进来了,见夫人也在,立在一边。裴卢氏连着两天现身丈夫卧房,裴居道心中不能不有感应。裴卢氏低眉顺眼,眼角余光还瞄着手边的佛经,神色平静,不似有什么欲念。那她今夜又来是凑巧吗?
洪甘姬说:“相爷,既然夫人在,甘姬退下了。”
裴居道说:“且慢。”他转头对裴卢氏道:“你们妯娌怎么不联床夜话?”
裴卢氏道:“族嫂清静惯了,不喜欢与人同睡。”
裴厍狄氏虽已中年,容颜甚美。她良宵独卧,提起来教人同情。裴居道想起深宫寡居的女儿,心中凄恻。然而裴厍狄氏寡居已有四年,姿容未减;女儿寡居十一年,方今不到而立,红颜是否尚在?裴居道心里又冒出了一点指望。
裴居道问:“晚餐时怎么没见到族嫂?”
裴卢氏道:“下午聊天时用了点小食,族嫂说已经够了,因此咱们用餐时她在佛堂礼佛。”
裴居道皱眉说:“你不会要在这安营扎寨吧?”
裴卢氏道:“府中房舍虽多,都颇狭小,我若去了别处,给族嫂看见,不大得体。”裴居道因为沉湎女色,广置姬妾,偌大相府渐渐填满,空房都是姬妾挑剩下的,逼仄可想而知。
洪甘姬小声说:“夫人若不便,可以暂住大郎夫妻的卧室,大郎住二郎的,……”
裴居道脑子里转了转说:“办法是有的。劳动太多。族嫂要在府中住多久?”
裴卢氏道:“她礼佛专心,误了宵禁,明日就回府了。”
待要逼妻子去睡最小的房间,当着孙子和姬妾,似乎说不出口去。族嫂在府中,迟早也会知道。
洪甘姬察言观色,见裴居道眉头舒展了又皱起来,说:“相爷,妾身回房了?”
裴居道挥手让她走。
他与孙子玩了一会儿,还是烧得难受。他已经过惯了放纵春宵的生活,手上摆弄着温润滑腻的玉如意,心思已到了帷帐之内。他神思不属,浮想连篇。过一会儿忍不住,拔脚去了洪甘姬的房间。
红尘逐浪不能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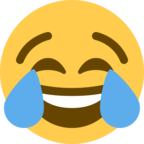
#8 Re: 关于隐痛
刘裴氏带雨奴来回拜裴卢氏。她们在佛堂聚首。
裴卢氏因为虔心礼佛,佛堂打理得很素净。壁上挂白衣观音,案上供香,香案下一叠佛经,地上几个蒲团,两个木鱼,两个槌儿,除此空无一物。
裴卢氏见雨奴目光逡巡,只在佛经上打转,问道:“你识字吗?可以拿起来读。”
刘裴氏道:“雨奴爱看传奇,你这些佛经恐怕她读不进去。”
裴卢氏抽出一本经说:“这些都是绘本,有绣像。要带小孙子嘛!”
雨奴道谢接过去翻开。刘裴氏问裴卢氏:“近来有什么心得?”
裴卢氏道:“魔鬼之言不能听信。”
刘裴氏道:“何谓魔鬼之言呢?”
裴卢氏道:“有的话语与经上的很象,然而似是而非,不细心分辨的话害人不浅。”
刘裴氏道:“你有例子吗?”
裴卢氏说:“同流合污就与和光同尘很象。劝人同流合污不是魔鬼之言吗?”
刘裴氏道:“人为什么会说一些害人转向邪恶的话?也许她曾经不幸,心中有很多苦,对世道有负面的看法。”
裴卢氏见刘裴氏目注雨奴,眼含疑问,就问道:“雨奴,你觉得呢?”
雨奴翻着绣像,听见叫她,放下佛经想想说:“不见得曾经不幸吧?人都有眼睛啊!看着什么样的人高升,什么样的人不得志,自然就会比出结论了。”
裴卢氏道:“这是因为眼睛看的方向错了。人的眼睛不该看着神佛吗?别人高升还是受苦,不都是尘世上的事情吗?”
雨奴说:“我们都活在世上,当然要看尘世的事情啊!”
裴卢氏道:“尘世的事情大多在低处。佛堂里看的是内心深处的东西,它高于尘世。“
雨奴道:“这个高低又是怎么算的呢?”
刘裴氏道:“这件事在我很简单。我有衣食住行的需求,也有对人的眷恋。我爱孩子,当把对孩子的爱和对衣食住行的贪恋放在一起时,爱孩子的心是更高的。”
裴卢氏道:“不错。如果你拿尘世的东西来与神佛的事情比,我要这个,我要那个,那就是骄傲,自以为自己与神佛并肩,那是魔鬼之心啊!”
雨奴不服气地说:“我没有骄傲呀?看的人多了,从中猜测众人的心意,那不是众人之心吗?众意不是与神意连着的吗?服从众意,别人要什么我也要什么,怎么能算骄傲呢?”
裴卢氏道:“如果你看到的众人之心都是物欲,你岂不是看到了众人的低处吗?你其实没有看到每个人所仰望的东西呀!”
刘裴氏道:“物欲又不是魔鬼之心。人谁不想吃美食,衣轻裘,住华厦?我们生就如此,只好安然接受。然而害人之心不可有,以物欲为最高并且宣扬它,那是魔鬼之心啊!”
裴卢氏点头说:“有时人说了害人的话,他自己不知道。虽然是魔鬼之言,不要因言废人就好了。”
刘裴氏道:“我遇到的又不同。我有时过于追求完美,而他人的行为与我的期待完全不同。这时我就陷于信仰与梦想的漩涡,何者更高就无法确定。可是以自己的梦想为高,不是骄傲吗?”
裴卢氏道:“神意、己意、自己的物欲都是不相同的。通常物欲低于梦想,梦想低于神意。有时梦想与神意相合,那还是应该追寻。在我,我爱女儿,不能相聚。爱而无能,只好当它是神意。”她信手敲了两下木鱼,目光垂了下去。
刘裴氏恻然,说:“我听人说,你仰望着神,神也会帮你。”
裴卢氏叹口气道:“是的,当我想到服从神意时,心中就好过一点。神佛已经帮助我很多了。”
刘裴氏也说:“人的幸运与坎坷哪是自己能主宰的?放下了就会愉快得多。”
三个人谈谈讲讲,又耽搁了晚饭。冬天黑得快,刘裴氏与雨奴共用了裴卢氏的卧房。裴卢氏又带着丫鬟走到裴居道的卧房。
开门进去,裴居道搂着奚衣姬,已经揭开了奚衣姬的衣领。见丫鬟推门让裴卢氏进来,裴居道忙把奚衣姬推开,整衣喝道:“走开!”
丫鬟解释说:“今夜刘夫人需要用夫人的卧房。”
裴居道说:“出去!”
他跳下床来推裴卢氏出门。裴卢氏避得慢了,被他推了个踉跄,丫鬟惊叫出声来扶。
刘裴氏与雨奴还没有入寝,听见响动,出门来望。裴居道满面怒气,拳脚方举,竟不能与刘裴氏打招呼,勉强点了一下头就缩回去关门。
奚衣姬见他回来,便宽衣解带,等着颠鸾倒凤。岂知裴相爷中道而返,不能成功。
试了两次,裴居道放弃了,颓然倒在奚衣姬旁边。
奚衣姬善解人意地说:“今日刘夫人带了位可人儿来拜访,相爷是不是移情了?”
裴居道黑暗中曾瞥了雨奴一眼,恍惚的确是个美人。他辗转了一会儿说:“你睡吧,我出去走走。”
他出了门,外间守夜的丫鬟绣锦连忙起身跟上来。裴居道趁黑在内宅里走了一遭,怒意渐平,走廊的寒风吹起他莫名的空虚。众人都已入睡,唯有一间小屋亮着灯光。
裴居道敲门进去,果然是裴卢氏在念佛。房屋狭小,丫鬟已经去别处与友伴挤了。裴居道立了一会儿,裴卢氏眉目不动,神色如常。
刘裴氏、雨奴的目光、裴卢氏的低眉、奚衣姬的身影交替在诵佛声浮现,安静又复杂的怜悯令他惶惶不安。屋角有小榻。裴居道遣绣锦回去,解衣上了榻,在木鱼声中躺了下来。
#10 Re: 关于隐痛
深夜裴卢氏熄了灯,在裴居道身边勉强歇下。裴居道醒了,就解裴卢氏衣襟。裴卢氏是裴居道妻子,尽了责任。
裴居道久不与裴卢氏亲近,觉得她可怜,停了一会儿,又想再做冯妇。岂知裴卢氏将他推开了。
裴居道十分惊奇,问道:“你不让我躺?”
裴卢氏不响,摸索着系衣裳,过会儿说:“不是裴相爷的床吗?”
裴居道在黑暗里笑了,说:“还以为你会念佛!”他又解裴卢氏的衣襟,裴卢氏又将他推开了。
裴居道摸不着头脑,说:“你什么意思?”
裴卢氏道:“郎君,色身是妾身自己的。”
裴居道没明白,说:“你欲拒还迎吗?”
裴卢氏道:“色欲伤身,郎君也要自重才好。”
裴居道说:“你以为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吗?”
裴卢氏见他说得露骨,不再答他,扭身闭目要睡。
裴居道没听到回音,以为裴卢氏已回心转意,又来琢磨裴卢氏的衣裳。裴卢氏一挣,“啪”地一下,手掌拂过裴居道的脸。
裴居道着了一下,火了,按住裴卢氏要霸王硬上弓。裴卢氏侥幸挣开,要下床,被裴居道拖回来。两个人纠缠在黑暗中,动作凌乱失控。裴卢氏眼见不敌,挣扎着说:“强暴!”
裴居道前两年刚刚参与修撰了《垂拱格》,立刻说:“律法没提婚内算不算!”
后世婚内强暴也构成强奸罪,读者请勿忽视这段话。不愿指证丈夫强奸的人可以寻找所在国的热线求助电话。
裴卢氏喘着说:“难,难,”她想说难道律法不管就不是罪孽吗?但她出力挣扎,心情激动,竟然话也说不完全。
裴居道已经几近得手。他虽然姬妾众多,但哪个不是曲意承欢?从未给裴居道机会让他展露蛮横。裴居道兴奋得发抖,妻子的身体忽然有了特别的魅力。一种陌生的爱意从他心底流淌出来,他感到久违的快乐。
他咬住裴卢氏的衣领,忽觉耳边发凉。他一时收不住势头,仰头将裴卢氏衣领扯开,随即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犹如兜头浇了一桶冷水。他直起腰伸手去摸。裴卢氏赶紧用放松的手推他。
裴居道摸了耳边是湿的,又摸裴卢氏脸上。裴卢氏拦阻不住,果然给他摸到眼泪。裴卢氏哭了。
裴居道不是凶霸的人,他教育子女也是照本宣科,讲孝悌友爱。他与裴卢氏少年夫妻,也不是没有过恩爱的时候。不如此何以能养出一位皇后?夫妻和合,进退已成默契。既然裴卢氏真的不愿意,那又何必强人所难?他倒在裴卢氏旁边,低声说:“别哭!我不知道你真不愿意。你空床很久了!”
裴卢氏流着泪待要下床,闻言一动,迟疑了一会儿。她下床走了几步,到门边摸着门把手,听听房中并无声息。
裴卢氏出身范阳卢氏名门,虽然年未半百,已是五个儿子的母亲,第一个孙子也已经出生。佛祖说万法皆空,是的,都是空的,她在无比的空虚中也依然需要考虑空虚。而慈悲与彻骨的哀愁同时临到她。
裴卢氏下了决心,又躺回来。过了一会儿,听得裴居道并未再来骚扰,裴卢氏低声说:“佛祖保佑。”
裴居道觉得可怜,又觉得后怕。刘祎之夫人还在裴府。明天早上见到裴卢氏妆容憔悴,岂能没有话说?方才鬼迷心窍,尘世的种种他完全忘了。他下床找出绢巾又给裴卢氏擦了擦脸才躺下。他也说不清是为了功利、抱歉还是真心实意。
#12 Re: 关于隐痛
火燃尽了才会自己熄灭。
裴居道在裴卢氏处得不到满足,辗转不能成眠。裴卢氏也没有入眠,她身体发僵,与裴居道相摩擦,裴居道的火又起来了。
裴居道忽然想起奚衣姬。自己一时不豫出了卧房,把衣姬留在了大床上。她应该还玉体横陈,等着他的爱抚,而且奚衣姬能陪他尝试新花样。
心火大炽,裴居道猛地坐起。
小屋外传来脚步声。这么晚了,月已过中天,谁在巡夜?裴居道停住了,支耳细听。
自从前太子李弘中道崩殂,裴妃无奈守寡,悲伤就降临到裴妃的娘家。裴卢氏怀着说不出口的求奇迹的指望,吃斋念佛,大行善事。
裴府的丫鬟都年迈,因为十年来没买过年轻丫鬟。旧有的丫鬟长大嫁人了,裴卢氏就招些孤苦无依的中老年妇人入府。她希望为自己不知所以的前世罪孽赎罪,为女儿祈福。因此裴府内宅的巡夜也都是些妇人,行动较方才过去的脚步迟缓。
裴居道并不清楚脚步声哪里有不同,他只是本能觉得不对。裴府深宅错落,裴居道夫妻眼下栖身的小屋在角落上。纵使巡夜,通常也走不到这里。
脚步声在门外逡巡了一会儿,在隔壁停住了。裴居道轻手轻脚下了榻,到门边细听。彼时窗户是纸做的,点破窗纸,便可以听到外面的风声。
裴居道听到一个男子压抑且急切的声音,低声叫着:“风姬……风姬……”
原来崔风姬住在这里!崔风姬也是裴居道的姬妾!这是私情!
裴居道满腔欲火霎时间转成了怒火,他冲到门边大喝一声推开门,就要去捉奸!脚下不知被什么一绊,跌倒在门槛上。外面的人受了惊,咚咚咚跑了。
裴居道爬起来到隔壁推门,门没有开。裴居道怒不可遏,攥拳头捶门,又上脚去踹,把门踹开。房中的女子睡眼惺松坐起身来,才点着了油灯。
裴居道冲上去把崔风姬的被子掀开,崔风姬惊叫了一声。她姣好的身材裹着黑色内衣,曲线毕露。裴居道直起身来站在崔风姬的房中,喘着气四下扫视,不知道要做什么。他参与编撰《垂拱格》,对律法有点了解。如今的情势,求奸者没找到,被引诱者意向不明,怎么办?
崔风姬一边扎着长辫子,一边颤声说:“相爷!怎么今夜贵足踏贱地!?”通常姬妾是应召去裴居道卧房的。裴居道深夜来访,事有可疑。
裴居道此刻没心情欢爱,他说了句:“你且睡!”一阵风般又出了门。
邻室里裴卢氏闭目向里,和衣而卧。裴居道关了房门,踱了一会儿,踢起地上散落的衣裳,丢在床顶。
裴居道长子裴汪已娶亲,又有小儿,四子裴瀜尚幼,内宅除了裴居道及四个儿子,没有其他男子。跑开的那人不是裴溓就是裴润,是哪一个?
刘裴氏还在府上。她与带来的姬妾在裴卢氏的卧房安睡。
刘裴氏是宰相刘祎之的妻子。
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难道裴相爷就这么不及刘相爷?不但才华不及,还家反宅乱,给刘相爷的家人看活生生的笑话?
裴居道放弃了立刻大搜的念头,回来坐在榻上,俯身向裴卢氏道:“你养的好儿子!”
裴卢氏很怕他再行强暴,紧贴着墙壁,手指抓着衣襟,默默颂佛。但裴居道没有。他的气息洒在裴卢氏肩上,怒火如焚。
不知过了多久,这火变成了烟灰,东方已白。
网上查裴居道只有四个儿子。从这一章改。
#13 Re: 关于隐痛
裴居道梳洗了走进厅堂,裴汪、裴溓、裴润都在座,连裴汪的儿子裴立心也在座。裴瀜还没来。
裴居道眼窝凹陷,询问的目光扫过三个儿子。他们都年轻,看起来都很可疑。
孩子们都象他一样,好身材,长方脸,眼睛里有想法,暧昧不明。
裴居道立了一会儿,咳一声说:“裴瀜怎么没来用餐?”
裴汪说:“还在睡吧?我带立心经过他窗下,缎娥还没开窗。”
绫罗绸缎娥是四个儿子的丫鬟。都是裴卢氏找来的孤寡老人,年纪很大。照顾裴立心的是丝娥,是孩子的乳母。丝娥虽然肤色黧黑,年纪可不老。她太普通。勾不起人的欲望。裴居道决定不怀疑她。
裴居道目光在几个儿子身上来回扫,“裴溓、裴润,功课还是应该捡起来。裴瀜也该早起,一日之计在于晨。”
裴溓笑道:“四郎不起床,二郎三郎赶上房。父亲,我已年近而立,在举子眼中,我是老头子了!”裴溓身材高大,脸孔白皙,头发却稀疏,发际线也在后退。他看起来象片经秋的叶子,形状都完好,只是似乎薄了。
裴润瞧见裴居道睡得不好,安慰道:“父亲,母亲不是常说一切由神做主吗?神要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您不用太着急。”他也重考科举两次了。但他肤色粉白鲜润,眼睛有神,虽然留了小黑胡子,倒比刮净胡子的裴溓看着有生气。
提起裴卢氏,裴居道火又起来了。他心中很复杂,他对妻子没什么特别的仇恨,又有欲望,但是妻子拒绝了他,他觉得受挫,无法象对待爱人一样想对方所想。他粗鲁地说:“让你们去考,就去考。”
裴瀜匆匆低头走了进来。他还没有及冠,但也不是小少年了。他个子高大,头发浓黑,身板还很单薄。他进来落座,锦娥递了碗筷,他立刻开始吃饭。
裴居道有种奇异的感觉,觉得昨夜去找崔风姬的就是裴瀜。他温和地说:“四郎!”
裴瀜停下筷子,慢慢抬起眼来,与父亲对视。
裴居道说:“风姬——”
裴瀜脸白了,“父亲是叫我吗?”他有种等待审判的紧张,脆弱又满身对抗。
裴居道说:“风姬唱得不错,她说曾经听过你的歌声。”他心里已经大致确定了。只有裴瀜才会这样急不可耐而又沉不住气。裴溓与裴润都晓得去青楼寻欢做乐,也不象裴瀜这么压抑。一晃四郎也要成年了。
裴居道看了给裴立心喂饭的丝娥一眼。丝娥是城外找来的农人,人很老实。她听到了多少?儿子不会撒谎,裴居道反而需要体面地解决这件事。如果不是裴瀜呢?又怎么办?
裴居道一夜未眠,眼袋明显。裴瀜的三个兄长都已觉察不对劲。裴居道虽未明言,三个儿子却有了大小、方向不同的想象。裴汪率先起身劝道:“四弟偶尔不用功,父亲不要太烦恼了。”
裴溓也说:“父亲平时就思虑太重。妹妹深宫守寡,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父亲也为此劳形。如今四弟唱歌也要被父亲念诵,太不值得了。”
裴润不象两个兄长那样能顾左右而言他。他说:“父亲,索性把四弟送去国子监读书也好!专心备考,也许能高中!”
一语提醒了裴居道,他随即说:“四郎功课还不够好。进国子监的话,太耗人情。”
裴瀜咬住嘴唇,过会儿说:“父亲,儿子不想入国子监!”
#14 Re: 关于隐痛
裴居道没有回应裴瀜的反抗。他说了一句:“我得去部里。回来后你到书房里来。”就去上朝了。
裴居道是宰相兼刑部尚书。他很厌恶刑部。刑部一方面总是要与犯人打交道,另一方面,审理犯人需要反复验证,同一件事来回地审,确认方方面面的细节。裴居道烦这种象裹脚布一样繁冗的啰嗦。刑部还管理监狱,监狱里的种种也让他受不了。
他去过几次天牢。当时狱官试图审问在押犯人,找出叛贼的同党。好好的人给折磨得不成样子。他看不下去,向天后密奏说谋叛大事,在天牢里审理,劫狱者有目标,在押犯都看得见。不如另找秘密地点,把谋反大罪的疑犯刑审、关押都挪走。天后因此把疑犯都提到留台。以后裴居道乐得卸责,遇上奇怪的犯人,都丢到留台,他落个眼不见为净。
眼下出了裴瀜的丑事,裴居道更加无心刑部事务,下朝后在部里坐了坐就去找北衙禁军首领李多祚。北衙禁军前几天出了伤亡,侍卫出缺。
北衙禁军一下子死了两个人,还有一个侍卫重伤。李多祚没要裴居道多费口舌就点了头。
裴居道与李多祚敲定了由裴瀜补任禁军侍卫,回府来发落儿子。
裴溓、裴润都躲出去了,这两个不孝的儿子,科举一塌糊涂,看风色比谁都精,象两尾滑溜溜的鲫鱼。裴汪事情忙,还没回来。裴瀜一叫就到,这次没有躲开。
裴居道带着一丝快意告诉裴瀜自己的决定。裴瀜接受得很平淡。
裴居道大出意外,问他:“你可想好了?”
裴居道列祖有镇守一方的刺史,也有兵部尚书。但自从天后大力拔擢寒族,科举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裴居道也希望儿子学业有成。他自己才学不够,从左金吾将军出身,还赖有女儿封妃之力。
如今让裴瀜去从军,相当于放弃科举了。
虽然仍在京畿,但从底层做起,裴瀜又冒犯了父亲,不知何年何月才有出头之日。裴瀜并不畏惧,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
裴瀜说:“多谢父亲代为营谋。”
裴居道说:“你不是不愿意出府吗?”
裴瀜说:“母亲说我年岁渐长,宜乎自立。”
裴居道又是意外。他说:“你娘原来管事。”
裴瀜看了裴居道一眼,闭紧嘴没有回答。
裴居道很快就知道为什么裴瀜那样看他了。他的烦恼又都冲着妻子裴卢氏了。
府中姬妾,全部不知去向!
奚衣姬、洪甘姬、尤烟姬、晁蔡姬、劳炳姬、乍枝姬、新首姬、殿世姬、筱尔姬、大印姬、计酸姬、孔迢姬、棉苞姬、冷引姬、贝石姬、崔风姬、透影姬、首阴姬、路银姬、陆相姬、窦姜姬、枝步姬、冯任姬、寇孔姬、丁书姬、肖琵姬、敬谐姬
二十七位姬妾,全被裴卢氏送进了善乐坊学乐理去了!
#15 Re: 关于隐痛
裴居道瞪着裴卢氏说:“你至少要跟我商量一下!”
裴卢氏抱着立心翻画册,口中说道:“裴瀜从军,郎君跟妾身商量了吗?”
裴居道说:“你知道你儿子干了什么事?”
裴卢氏闪避了,说:“妾身虽然有一点冒失,但善乐坊同在洛阳城内。郎君需要的话,随时可以把她们接回来。”
裴居道鼻子里哼了一声说:“裴某身居相位,岂能出尔反尔?外间只知道裴相府发落了姬妾又把她们找回来了,可不知道送是主母,接的是主人。”
裴卢氏道:“既然如此,郎君稍安勿躁。此次培训为时一个月,很快就都回来了。既不兴师动众,又不耽误郎君的清兴。”
裴居道待要再说,裴卢氏抱起裴立心朝着裴居道,裴立心张口说:“佛祖。”
裴居道一震说:“会说话了!”
裴卢氏笑眯眯地说:“是啊!立心,说菩萨!”
裴立心说:“菩哈!”
裴居道忘了烦恼,眼中有了笑意。他忍不住盘膝坐下。裴卢氏忙把另一个蒲团拽过来递给他。佛堂里清素,该添点东西。
裴居道逗裴立心说:“爷爷!”
裴立心抬头看裴居道,说:“鳖鳖。”
裴居道没怎么费劲就想到了一个常被用于骂人
的动物。他脸上一热,心沉了下去。
裴卢氏眼角一弯,没笑,说:“爷!你瞧,嘴唇不要碰。”
裴居道问:“保姆怎么没跟着?”
裴卢氏道:“立心差不多可以断奶了,又冒话儿。跟着我多念点佛经好些。我让人送丝娥回乡下了。”
很多事裴卢氏不在场,但她的处置却似乎与府中种种都相关。
裴居道勉强坐了一会儿,站起来抬脚走了。
#16 Re: 关于隐痛
裴瀜收拾衣装去了禁军。转头裴居道很快发现裴卢氏已经做好了对付他的准备。而且这准备得到了儿子裴汪夫妻的支持。
夜里他独睡寂寞,到裴卢氏卧房中去找她,赫然发现孙子裴立心也在!
他在裴卢氏身后躺下来,裴卢氏动了一下,一只手背过来推拒。
裴居道抓住她的手,放在自己胸腹之间,停了片刻,伸出自己的手来抚摸妻子。
裴卢氏惊颤了一下,低声说:“孩子。”
裴居道向前摸索,很快摸到了立心的脚丫儿。他忍住煎熬缩回手,把裴卢氏紧紧地抱在胸前。
也许裴卢氏感受到了他炽热的渴望,她拉了他一下,悄悄起身。
裴居道心有灵犀,起身随裴卢氏到自己的卧房。两个人宽衣解带,相亲相爱。
逸兴方歇,裴居道还在沉醉,妻子已经匆匆离去,连衣裳都没顾上拿。等裴居道醒觉追出去,妻子的卧房上锁了!
裴居道不是大吵大闹的人,撼了两下门,颓然回房。
丫鬟绣娥惊醒了,点亮了烛火问:“相爷还不睡吗?”
裴居道心中一动,看绣娥一眼。不行!太老了!裴居道没胃口!
第二天裴居道找个机会对裴汪说:“立心要多跟着他娘。”
裴汪说:“哦?”
裴居道说:“学讲话了。跟着奶奶尽学些佛祖菩萨的,别给外人笑话。”
裴汪说:“父亲,阿娘日常来往的夫人们都是信佛的。不会笑话。”
裴居道说:“朝廷官员可未必信佛。”
裴汪说:“朝廷官员又不进内宅。”
裴居道一看此路不通,改从另一个方向发力:“孩子需要娘,总跟奶奶一起睡成什么话?”
裴汪说:“父亲真在意这件事,晚餐时再讨论。”
裴汪是兰台秘书郎,管理皇家图书典籍。图书浩如烟海,读一遍都读不完。秘书郎这个工作,想偷懒很容易,想忙肯定是有的忙的。
裴居道跑到兰台来跟儿子讲闲话,有一点逾矩。他理亏,只好回府了。路上一想,儿子这是耍他啊!
立心跟谁睡觉,需要裴溓、裴润参与讨论吗?
再一想,裴汪是拐着弯儿怪他不该在餐桌上提裴瀜的丑事啊!可他那时连是谁去找了崔风姬都还不知道!
从老到小,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形成了保卫裴卢氏卧房的联盟!
#17 Re: 关于隐痛
下一个晚上,裴卢氏又一次拒绝了裴居道。这次裴居道一点荤腥也没沾着。
裴居道不是自甘轻贱才一再找裴卢氏求欢。裴卢氏把二十几位姬妾都送走了,难道不是想要他吗?
是,是有裴瀜的丑事。但她既然把人都送走了,她作为妻子,难道没有承欢的义务吗?
裴居道非常难熬,好象有把扇子在他脑子里不紧不慢地扇,扇得他头脑中的火四下吐着火舌,却觅不到出口。他在床上安卧,他头脑中的自己却在翻滚,用各种想象来刺激自己,来得到片刻的快慰。
他想念奚衣姬高大的身材,洪甘姬温暖的体温,他想念尤烟姬健硕的胸脯。他喜欢晁蔡姬叽叽喳喳的私房话,劳丙姬柔软又有弹性的臀部,窦姜姬硬实得按不下去的大腿。还有崔风姬不盈一握的腰肢,敬谐姬欢迎的眼神。他喜欢乍枝姬芬芳的气味、有什么说什么的水晶心肝,新首姬的精致衣品、总爱躲猫猫的淘气。
他怀念殿世姬招之即来的痛快,筱尔姬猫一样的耳鬓厮磨,大印姬说话前习惯性的轻笑。他也不能忘记计酸姬断了气一样的高潮,孔迢姬清冷的回眸,棉苞姬总在薄暮中出现,轻软的身体让人爱怜,冷引姬则是夜晚最沉默的星辰,人如其姓,她有一种沁人心脾的冷。
他喜欢贝石姬总是半句话留白,透影姬暧昧的调情。他在梦里听到首阴姬怀旧的咏叹调,想起路银姬一字不漏听他讲话,陆相姬讲起故事来滔滔不绝,枝步姬有条不紊的迎合。他怀念冯任姬挺直的背脊,寇孔姬在不失风情的娇嗔。
他念着丁书姬的字迹,像她自己——独立、不羁、带着一点忧郁;肖琵姬总在他心头泛起一段旋律,是他始终没写完的结尾。裴居道不单是出于欲望想念她们,这些人从他身边走过,每一个细节,都在他的心里留下一片不能磨灭的风景。
他当然也想念他的妻子裴卢氏。他妻子清瘦单薄,肤色白皙,缩肩,鬓边已有白发。裴卢氏与他的姬妾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他的姬妾都正在年轻,有一种不知世事的蒙昧,平淡又漠然。他妻子却是有灵的,他知道她疼爱孙子,心疼女儿,因为怜惜而开心不起来。如果说他的姬妾们灵性尚在潜藏中,他的妻子却因为与他共有的年华而被他窥见了所有前因后果,因而她的灵性他能看见,近得可以触摸。
他对妻子有欲望,想起那次抓住她,她象手心里的小鸟一样惊慌地扑着翅膀,裴居道浑身发热。
他什么都逃避,他的妻子突然成了一个出口。他可以经由操控她的喜怒哀乐而感到无比的满足,觉得自己真是一个男人,能够施予给他的爱人。他有能力给她快乐,他在与她做爱。而当她惊慌失措的时候,他促狭的捉弄心也得到了释放。他感觉自己是优越的,即使妻子怜悯他,他依然有妻子不能忽视的权威。他靠女儿上位做宰相也没关系;他厌恶自己的刑部也没关系;他没办法把两个不成器的儿子送出去也没关系;他被小儿子戴绿帽子也没关系;他不忍心处罚儿子也没关系;他被全家上下鄙视也没关系。他俯视她,居高临下。
他绝不是出于残虐、报复心而产生的欲望。他深信与妻子做爱是彼此有益的。裴卢氏做爱后脸上有两团红晕,她又老了,眼角有皱纹,灯下看着有点俗气。但是第二天她看起来很水灵,好象红晕均匀地散进了她的身体里,让她整个人都多了生机。这样有什么不好吗?
但是她显然不吃他这一套。她把裴居道的姬妾送走,而她以孙子裴立心为盾,关上了卧房的门。
#19 Re: 关于隐痛
关于格
后世有个词,叫做“格调”。从后世人的眼光猜测,裴居道是个很有格调的人。
人们常常说这个人那个人有格调,不说他们有人格,是因为人们总觉得对物质需求的格调不够高尚。
基督徒说道永恒的荣光,把希冀寄托给神,这毫无疑问是高尚的。有人为人处事有一定之规,一定不会贪污,不会腐败,这也是高尚的。
但高尚的东西不接地气。放大镜下面没有完人。从一个人自相矛盾的地方开始灵魂拷问,可以让人羞耻至死。在快节奏,恋爱都来不及的后世,谈道德有用吗?不都只是限制而已吗?金钱、权势、名望,谁不想要吗?所以别和我谈人格吧!
道德是外在的束缚,但它也可能是内在的力量。这一点,只有在对自己立场的反面有清晰了解后才可能达成。
以后世人的眼光看来,裴居道的出身相当于后世的富二代。虽然他没什么追求,对物质也没有特别的留意,但他是有要求的。
他之所以没意识到自己有格调,是因为高水准的物质条件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他也许喜欢骑肥马、衣轻裘,但他并不需要主动去选择肥马轻裘,他的父辈就是这么生活,虽然当时有很多人甚至没有马或裘。
在性这件事上,可以推理出面对挑战时,他也是有格调的,这与骑肥马、衣轻裘有点不同。故事里他姬妾众多,他对性很了解,一定知道他还有其他选择。可他没有选择其他。
他的品味与格调使他不至于失态。难道格调也有道德约束力吗?
不是。后世西方作家王尔德的故事里,亨利爵士就是一个优雅的恶棍。格调不能妨碍他拉别人下水。
但是裴居道也许特别幸运一点。他被自己的格调拦住了。
如果裴卢氏把姬妾送走,对裴居稻坚壁清野,然后裴居道失去自持,做出哀求、讨好、依附等事来,那裴居道会众叛亲离,甚至影响到他的声誉,在冤死之前已经被天后斥退。
人要能控制自己的欲望,性欲与物欲都是如此。
然而诱惑的力量那么大,后世有多少人沉溺于感官刺激的内容,漫不经心地被诱惑牵引。
不谈人格,谈谈格调也是好的。人格与格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人格是一种深层的道德意识,格调是物质上的品味。然而它们又有相通之处。它们都是自发的选择和拒绝。也许从有格调开始,真的慢慢构筑出人格来呢!说到底,人该建立有时说“好”,有时说“不”的行为习惯。而这行为习惯最好能反映他的真实心意。唯有这样,外在的道德约束也好,内在的人格力量也好,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