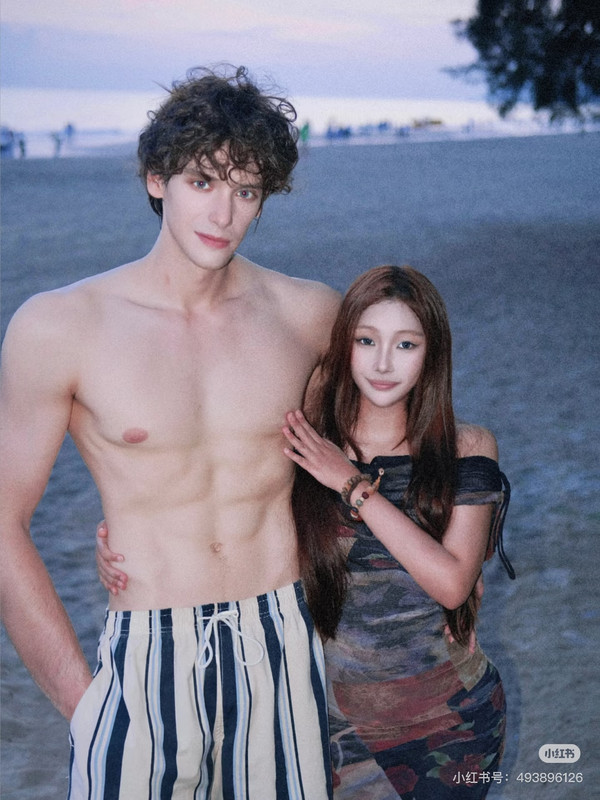#1 中国尚未准备好承担全球领导角色
发表于 : 2025年 7月 7日 00:33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5/07/04/ch ... americana/
美国治下的和平已不复存在,但中国治下的和平却遥遥无期。
过去几个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华盛顿外交政策的深刻调整引发了一场争论,即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自我毁灭在多大程度上赋予了中国力量。“美国收缩有利于中国崛起”的观点已得到充分论证。然而,尚不清楚的是,特朗普是否正在为一场更为根本性的转变铺平道路:以中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取代支离破碎的美国主导秩序。
华盛顿的撤退显而易见。特朗普对二战以来美国总统为维护美国利益而建立的秩序和机构发起了系统性攻击。华盛顿大幅削减全球贸易,大幅削减联合国经费,缩减对外援助,并激怒了许多关键盟友。通过掏空国家安全机构,特朗普有可能削弱华盛顿的战略能力。北约和其他美国精心打造的联盟的未来尚不明朗。特朗普宣布对大学和主要科研机构进行全面攻击,可能会动摇美国实力的根基。
将美国后退与中国崛起联系起来的论调由来已久。随着力量平衡的转变,这种论调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拥抱资本主义。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其1987年出版的开创性著作《大国的兴衰》中指出了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20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的威廉·H·奥弗霍尔特是众多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将很快催生另一个超级大国的人中的第一个。
尽管如此,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并没有改变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华盛顿继续推行深度参与的宏大战略,以促进自由国际秩序。
“中国崛起、美国衰落”的下一阶段论调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展开,其根源和震源无疑都来自西方。这场动荡促使《经济学人》杂志发表“资本主义陷入困境”的言论,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也对其经济模式提出了严肃的质疑。北京对其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模式重拾信心,而所谓的“北京共识”作为西方经济和政治方案的替代方案,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广泛认同。
当时,美国的力量仍然远超中国,但马丁·雅克2009年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终结与全球新秩序的崛起》一书的书名,却捕捉到了当时的情绪变化。当时,我作为驻北京的外交官,亲眼目睹了中国共产党干部乃至整个国家日益增强的自信。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中国的外交政策便变得更加强硬。
第三个话语阶段始于2017年。同年1月,特朗普首次就职仅几周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了新的中国大战略。在中国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一个为讨论外交事务而召开的高层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为中国放弃之前的大战略奠定了基础。该战略由邓小平在20世纪90年代初制定,呼吁在国家富强的同时,在地缘政治事务中保持韬光养晦。习近平的新战略将采取积极的修正主义方式处理国际事务。这一战略转变在同年晚些时候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北京的领导层明白,中国现在正崛起为一个与美国地位更加平等的超级大国。北京的转变反映在国际社会关于世界重返两极权力格局(美国和中国是两个超级大国)的辩论中。
第四阶段,也是最新的阶段,始于特朗普今年重返白宫。批评人士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就已指出,他的“美国优先”政策是送给华盛顿对手的礼物,但当时,他的政府并未真正践行“脱离接触”的口号。这一次,特朗普真的在撕毁美国数十年的外交政策及其赋予美国的权力优势。如果说中国领导人在2008年就意识到力量平衡正在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变,那么我们今天可以想象北京权力中心的欣喜之情。
鉴于新的两极权力格局,华盛顿的全球主导地位已成过去。此外,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在美国政坛的兴起,是一个国家相对衰落的常见迹象。(事实上,美国右翼政治的当前议程与19世纪90年代英国右翼的议程并无太大不同,当时全球“大英治世”的终结已成定局。)通过积极且彻底地让美国脱离维护全球秩序的轨道,第二届特朗普政府正在加速权力向中国倾斜。
然而,即使美国全面撤退,也并不意味着北京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事务的主导力量。主要有四大原因阻碍了这一进程。
首先,无论其参与程度如何,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倾向于认真尝试削弱中国的力量。特朗普或许正在将华盛顿从全球治理机制中拉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准备屈居于次要地位。相反,美国似乎决心通过各种政策来维持甚至可能加强其相对于中国的强势地位,包括关税、制裁、旨在加强海上造船业的新出台的《船舶与安全法案》(SHIPS Act)以及旨在促进美国半导体研究和制造的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 。
其次,中国超级大国地位的性质与美国以及大英帝国等前超级大国截然不同。中国几乎不可能建立起与美国同等规模的全球军事态势。即使在今天,美国仍在约80个国家/地区拥有约750个军事基地和设施。中国总共拥有两个海外军事设施:位于非洲的吉布提支援基地和位于柬埔寨云壤海军基地的联合后勤和训练中心。中国当然有兴趣在海外建立更多军事基地,但北京要建立起类似美国的海外态势,仍需付出漫长的努力。
美国治下的和平已不复存在,但中国治下的和平却遥遥无期。
过去几个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华盛顿外交政策的深刻调整引发了一场争论,即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自我毁灭在多大程度上赋予了中国力量。“美国收缩有利于中国崛起”的观点已得到充分论证。然而,尚不清楚的是,特朗普是否正在为一场更为根本性的转变铺平道路:以中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取代支离破碎的美国主导秩序。
华盛顿的撤退显而易见。特朗普对二战以来美国总统为维护美国利益而建立的秩序和机构发起了系统性攻击。华盛顿大幅削减全球贸易,大幅削减联合国经费,缩减对外援助,并激怒了许多关键盟友。通过掏空国家安全机构,特朗普有可能削弱华盛顿的战略能力。北约和其他美国精心打造的联盟的未来尚不明朗。特朗普宣布对大学和主要科研机构进行全面攻击,可能会动摇美国实力的根基。
将美国后退与中国崛起联系起来的论调由来已久。随着力量平衡的转变,这种论调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拥抱资本主义。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其1987年出版的开创性著作《大国的兴衰》中指出了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20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的威廉·H·奥弗霍尔特是众多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将很快催生另一个超级大国的人中的第一个。
尽管如此,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并没有改变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华盛顿继续推行深度参与的宏大战略,以促进自由国际秩序。
“中国崛起、美国衰落”的下一阶段论调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展开,其根源和震源无疑都来自西方。这场动荡促使《经济学人》杂志发表“资本主义陷入困境”的言论,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也对其经济模式提出了严肃的质疑。北京对其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模式重拾信心,而所谓的“北京共识”作为西方经济和政治方案的替代方案,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广泛认同。
当时,美国的力量仍然远超中国,但马丁·雅克2009年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终结与全球新秩序的崛起》一书的书名,却捕捉到了当时的情绪变化。当时,我作为驻北京的外交官,亲眼目睹了中国共产党干部乃至整个国家日益增强的自信。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中国的外交政策便变得更加强硬。
第三个话语阶段始于2017年。同年1月,特朗普首次就职仅几周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了新的中国大战略。在中国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一个为讨论外交事务而召开的高层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为中国放弃之前的大战略奠定了基础。该战略由邓小平在20世纪90年代初制定,呼吁在国家富强的同时,在地缘政治事务中保持韬光养晦。习近平的新战略将采取积极的修正主义方式处理国际事务。这一战略转变在同年晚些时候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北京的领导层明白,中国现在正崛起为一个与美国地位更加平等的超级大国。北京的转变反映在国际社会关于世界重返两极权力格局(美国和中国是两个超级大国)的辩论中。
第四阶段,也是最新的阶段,始于特朗普今年重返白宫。批评人士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就已指出,他的“美国优先”政策是送给华盛顿对手的礼物,但当时,他的政府并未真正践行“脱离接触”的口号。这一次,特朗普真的在撕毁美国数十年的外交政策及其赋予美国的权力优势。如果说中国领导人在2008年就意识到力量平衡正在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变,那么我们今天可以想象北京权力中心的欣喜之情。
鉴于新的两极权力格局,华盛顿的全球主导地位已成过去。此外,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在美国政坛的兴起,是一个国家相对衰落的常见迹象。(事实上,美国右翼政治的当前议程与19世纪90年代英国右翼的议程并无太大不同,当时全球“大英治世”的终结已成定局。)通过积极且彻底地让美国脱离维护全球秩序的轨道,第二届特朗普政府正在加速权力向中国倾斜。
然而,即使美国全面撤退,也并不意味着北京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事务的主导力量。主要有四大原因阻碍了这一进程。
首先,无论其参与程度如何,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倾向于认真尝试削弱中国的力量。特朗普或许正在将华盛顿从全球治理机制中拉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准备屈居于次要地位。相反,美国似乎决心通过各种政策来维持甚至可能加强其相对于中国的强势地位,包括关税、制裁、旨在加强海上造船业的新出台的《船舶与安全法案》(SHIPS Act)以及旨在促进美国半导体研究和制造的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 。
其次,中国超级大国地位的性质与美国以及大英帝国等前超级大国截然不同。中国几乎不可能建立起与美国同等规模的全球军事态势。即使在今天,美国仍在约80个国家/地区拥有约750个军事基地和设施。中国总共拥有两个海外军事设施:位于非洲的吉布提支援基地和位于柬埔寨云壤海军基地的联合后勤和训练中心。中国当然有兴趣在海外建立更多军事基地,但北京要建立起类似美国的海外态势,仍需付出漫长的努力。